
法國電影理論家麥茨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與電影》一書中探討影院機制和觀影心理時,突出了三個關鍵字:認同、窺視、戀物。如果不惜折損麥茨理論的複雜性與深刻性,我們可以對這三個關鍵字作通俗化解讀——觀眾的觀影愉悅來自這樣幾個方面:被影片中人物的性格、處境、命運所吸引,或對扮演該人物的演員有認可與讚賞心理(認同);觀看奇觀性景象或隱秘、禁忌性內容的滿足感(窺視);對電影中的藝術技巧、藝員、電影衍生物(如海報、電影周邊、藝員簽名)等的迷戀(戀物)。在這種理論視野的照拂下,《古董局中局》的藝術得失就非常明顯。
《古董局中局》圍繞劇中人物許願與藥不然對唐代明堂玉佛頭的爭奪展開情節,雜糅了尋寶與冒險的元素,帶有懸疑與喜劇的色彩,結局是代表正義的許願與烟烟揭開了驚世謎底,粉碎了藥不然的篡位陰謀。影片為我們展示了古董界的深不可測、明爭暗鬥,鑒定古董的精妙與細膩,以及圍繞古董鑒定、買賣而發展出各路人馬與江湖格局,這足以滿足觀眾的窺視欲。影片中那些令人大開眼界的古董文物、各種機關和暗語、擁有較高人氣的藝員,多少可以撫慰觀眾的戀物心理。但是,觀眾觀賞一部影片的心理愉悅首先建立在認同的基礎上,即觀眾對人物有同理心、有代入感,對影片情節能產生沉浸感,不會質疑其中的邏輯。遺憾的是,《古董局中局》在召喚觀眾的“認同”方面幾無建樹,人物缺少感染力,情節四處漏風,觀眾的觀影體驗可謂疏離和抗拒。

電影中的玉佛頭
影片最大的看點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許願和烟烟在尋找真正的佛頭時,需要破譯諸多密碼,拼凑各種線索,這是對人物智商的考驗;二是許願和烟烟在“按圖索驥”時,需要面對藥不然的惡性競爭,對付老奸巨猾的付貴,擺脫老朝奉派來的追兵,並與鄭國渠的制假團夥纏鬥不休。按理說,影片可以借此為觀眾奉上智力衝浪和動作奇觀的雙重享受,並製造張弛有度的情節節奏,然而,當影片用空洞的人物形象、錯亂的人物動機、潦草的情節邏輯來結構時,觀眾像陷入了一團迷霧中,被各種應接不暇的人物衝擊得頭昏腦漲,不明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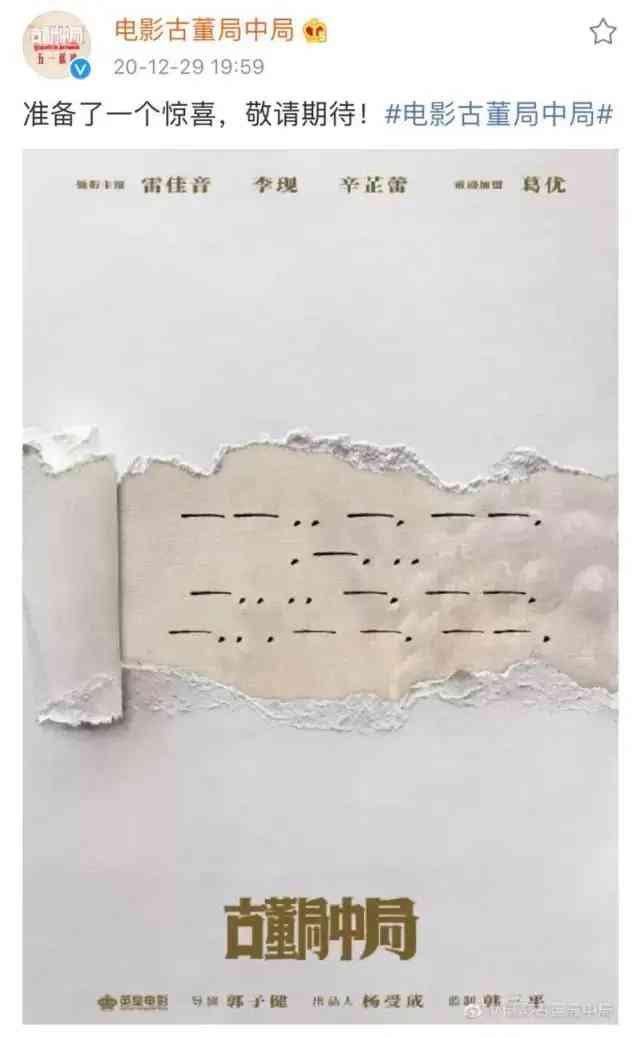
影片主人公許願一路尋寶,需要懂摩斯碼,精通篆書和中國古代文化,對圍棋知識和歷史如數家珍,當然還要在古董鑒定方面有極高造詣。問題是,許願7歲時父親就不辭而別,他寄人籬下,一直是被作為一名家電維修人員來培養的,少了父親的言傳身教和耳濡目染,又活得渾渾噩噩,他何以能建立如此廣博深邃的知識體系?許願的父親隱姓埋名,是希望兒子過上簡單平淡的生活,但他又留下無數線索,指引兒子找到佛頭,這本身也自相矛盾。
許願在歷經艱險,甚至死裡逃生之後,知道了一個“驚天”秘密:他爺爺當年將真佛頭包在假佛頭裡送給了日本人。觀眾等了兩個小時,隨同人物完成了一路的奔波和冒險,影片就端出了這樣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重磅炸彈”,這種一脚踏空的失落感令人沮喪。因為,縱然外假內真,許願的爺爺還是把真佛頭給了日寇,被槍斃,不冤啊。許願在會場那驚天一錘,卻生生坐實了自己爺爺的罪名,恐怕與想要給觀眾反轉驚喜的初衷背道而馳。
許願用驚人的洞察力和過人的智商,一路破譯父親留下的線索時,觀眾理應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的。但這個破譯過程依靠大量的“偶然”勉强維繫著,破譯之後又由更多的“巧合”來推動情節發展,這無異於沙上建房,根基不牢,故事塔樓隨時會傾覆。例如,許願看到父親房間裏真假混雜的古董時,瞬間想到摩斯碼。由於缺乏前期鋪墊,人物的這個腦回路多少有點突兀。他從摩斯碼中拼出“付貴”之後,一旁的烟烟馬上說她知道付貴,這種巧合簡直是天賜良機。他破解父親留下的摩斯碼之後,沒有破壞現場以誤導後來者,讓藥不然得以一路跟踪,這又顯得太不專業。他拿到青銅鏡的全部資料卻對關鍵資訊不甚明了時,一旁偷聽的付貴馬上說,覈心密碼是找鄭虎,而他剛好認識鄭虎……影片情節設定的隨心所欲、情節鏈條之脆弱牽強顯而易見。

葛優在電影中飾演付貴
“古董局中局”的片名相當於與觀眾簽下了合約,即人物形象、情節發展會存在意想不到的反轉和顛覆,一些看似平常的場景可能隱藏著令人拍案叫絕的騙局與算計。但是,影片中的“局”實在太少,精巧性不足,格局也不大。在關鍵性的尋寶段落中,人物不是身陷謎團中不知出路,不是因別人的陰謀而危機四伏,而是與敵對團夥正面對決,甚至在地洞裏爆發了激烈槍戰。一部以“做局”為賣點的電影,爭端的解决居然靠不合常理的槍戰,這已然落於下風。觀眾沒有在謀篇佈局中看到歎為觀止的“珍瓏棋局”,自然也無法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反轉中,湧動自歎不如的心理折服。
影片的開頭有一場民間拍賣會,發生在一家廢棄的工廠裏,折射了20世紀90年代國企改制的社會背景;許願開設家電維修店的那條小巷,寒酸破敗,形象地展現了當年下崗工人的困窘處境;許願出場時,落魄潦倒,醉酒度日。這些場景給觀眾一種錯覺,以為影片想對普通人的生存狀態表示人道關懷,或者書寫失意者步步艱辛的突圍之旅。不過,影片很快就讓許願離開這個晦暗的環境,走上驚險刺激的尋寶之路。這說明,創作者對於影片作為商業片的市場定位非常明確。只是,影片既然標明了“1992”的時間座標,就應該體現對時代人心的敏銳捕捉,對時代風情更有質感的表現與開掘,而不能一方面營造逼真的時代氛圍和濃郁的市井氣息,另一方面又沉浸在背景架空的敘事快感之中,甚至希望情節的展開不受現實邏輯的約束,更不受時代氛圍的禁錮,這未免有點自我分裂。這也解釋了影片敘事失控、觀眾出戲的原因,因為影片在創作之初就陷入了規劃與實施南轅北轍的困境之中。
評論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