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當人們談論起愛滋病,最根深蒂固的反應,是恐懼。愛滋病人手持針管紮傷行人、春宵一夜之後遭惡意傳染,此類新聞難辨真假,每隔一段時間便會刷屏我們的社交網絡。人們的“恐艾”心理,使得此類資訊自帶巨大的傳播力。
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社會文化的影響下,愛滋病已經不單純是一種疾病。它充滿了無數隱喻與聯想:濫交、吸毒、賣血,抑或是同志。它是死亡的信使,是人類的敵人,也被釘在了“耻辱柱”上。
誠然,愛滋病令人類恐懼,它深植於我們對死亡和痛苦本能的抗拒之中。但是,面對即使是無法根除的恐懼,我們也並非無能為力。你認為,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對愛滋病的恐懼?如果這恐懼無法根除,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
本文原發於2018年12月1日的書評週刊公號。
01
與愛滋病人同桌吃飯
恐懼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克服?
“我約到了採訪對象,他是一名愛滋病人。”
大三那年,紀錄片課的期末工作要求我們分組製作一部完整的片子。選題方向比較冷門,採訪對象非常不好找。這時,我們聯系到了一名願意出鏡的愛滋病人。
在那之前我們都沒見過真正的愛滋病人。它是生物課本上的一個名詞,是高考必背的考點:HIV,愛滋病病毒,RNA病毒,攻擊人體淋巴系統裏的T細胞;AIDS,愛滋病,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血液、體液傳播;後期會因免疫系統全線崩潰併發嚴重疾病,一場小感冒都可能奪走患者的生命……
定下採訪時間和地點後,我們商量了採訪提綱和報導倫理問題。想起某比特老師學生時代也做過愛滋病人報導,完成以後採訪對象同意發表,可老師還是選擇按下不發。多年後採訪對象在離世前聯系他說:“謝謝你,為我保留了最後的尊嚴。”如果我們將要面對的,也是這樣一個脆弱敏感、不忍拒絕的人,我們要怎麼做,才不會傷害到他?除了這些擔心,我們也有另外一種不安。採訪前,我檢查了自己,身上沒有傷口,口腔裏也沒有潰瘍。

電影《最愛》劇照,劇中主人公因賣血感染愛滋病。
採訪過程比想像中順利,採訪對象們意外地很開朗。一比特採訪對象家境還可以,有錢吃藥,病情控制得很好,父母也比較支持他,除了日常工作,他還在做愛滋病相關的公益活動。另一比特採訪對象醫保在老家,可那裡的醫院排斥愛滋病患者,很多檢查只能在北京做。他是孤兒,感染以後即使有醫保報帳,藥物費用對他來說仍然是一筆不小的負擔,言語間他流露出對前一比特採訪對象的羡慕:“他吃的是好藥。”
藥物可以控制病情發展,讓患者正常生活。可再好的藥也有副作用。初吃藥的愛滋病患者身體會有比較强的反應:整夜頭疼失眠,睡夢裏也是噩夢交纏。“愛滋病人不會害怕看恐怖片,因為更恐怖的夢裏都經歷過了。”身體上的病痛還能扛,最難的是在心理上接受自己患艾的事實。“家人和伴侶的支持很重要。”撐過了最難的階段,生活會慢慢好轉。
當天的幾比特採訪對象都是樂觀可愛的人,他們的笑容很能感染人。採訪中,我們在一起吃了頓飯。做飯的是其中一位採訪對象,飯菜很可口。
片子完成以後,我們尊重採訪對象們的意願,只在班級範圍內放映沒有公開。這次短暫的接觸也讓我重繪了對愛滋病人的看法:他們可以正常工作,可以正常生活,現有的醫療科技已經可以控制病毒載量,讓他們與常人無異。我不得不承認,在採訪前,我的內心並非毫無芥蒂,因為我從未在生活中接觸過愛滋病人,而未知往往伴隨著恐懼。
這次經歷也令我思考: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克服對愛滋病的恐懼?
02
患艾,是一種“懲罰”?
愛滋病的疾病隱喻
大多數人在生活中很難有接觸愛滋病人的機會。我們對於愛滋病的瞭解多來自於影視作品或新聞報導。而這些文字中,經常出現愛滋病的“懲罰隱喻”。
隱喻,實際是人們理解事物的管道,通過將不瞭解的事物與熟悉的事物相聯系,從而獲得未知事物在內心的定位。人們對於疾病的認識,經常以隱喻的管道進行。比如,肺結核在歷史上曾被視為一種“天才病”,肺結核病患者往往面目蒼白、情欲高漲,患者有一種當時的流行審美中別樣的優雅風範,“情欲高漲”的臨床表現讓人們誤以為肺結核的病因是內心的熱情湧動的結果。詩人拜倫曾說過,如果要死亡,他寧願患肺結核過世。
醫學的發展會抑制這種浪漫化的聯想,但現代醫學邏輯卻導致了新的疾病隱喻——懲罰隱喻。現代醫學研究發現,很多重大疾病,都可以從生活中找到誘發的原因。比如,癌症多是因為不健康的生活習慣:肺癌是因為吸烟,胃癌是因為飲食不健康不規律……換言之,疾病是一種“懲罰”,是自己日常不管束自身行為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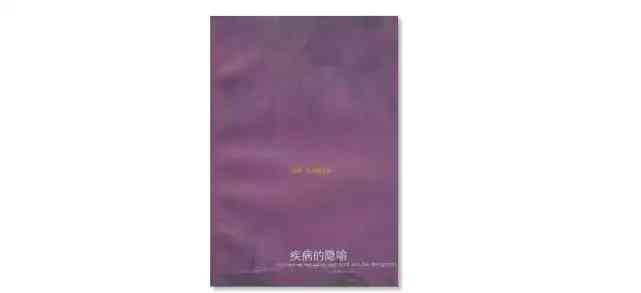
《疾病的隱喻》,[美]蘇珊·桑塔格著,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12月。
這種對於疾病的懲罰式隱喻,會深深折磨患病之人。曾經有一個朋友身體有問題去看醫生,醫生說他這個問題是天生的,與生活習慣無關。朋友說這讓他輕鬆了很多——這身毛病不是他熬夜熬出來的。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也提到,對於癌症的懲罰隱喻讓患者無法從容地進行治療,他們會陷入巨大的自責和愧疚之中,然而我們為什麼不能只把它當作一場病?正如尼采在《曙光》中寫道:“想一想疾病(本身)吧!去平息患者對疾病的想像,這樣,他就至少不必因為胡思亂想而遭受比疾病更大的痛苦。”
而愛滋病群體所承擔的痛苦,要更甚於一般疾病。他們不僅要因隱喻中的行為不當而自責,同時也要承受背後的道德批判。

香港電影《應召女郎》劇照,圖為馮寶寶飾演的主婦美鳳。
在1988年香港電影《應召女郎》中,馮寶寶飾演的主婦美鳳為了應付丈夫高額的醫療費用,瞞著丈夫兒子做應召女郎,不幸染上了愛滋病。後來,她又把愛滋病傳染給了丈夫和兒子,最後開槍自殺。2011年顧長衛的電影《最愛》將鏡頭對準了愛滋病村,蒙蔽落後的村人賣血掙錢染上了愛滋病,“血頭”的父親內心有愧,把染病的村民集中到廢棄小學中統一照顧。在這個疾病孤島中,生命倒數計時中的村民還在貪欲的驅使下勾心鬥角。
這些作品將愛滋病人的身份限定於特定的邊緣人群之中,意圖通過他們的故事表現社會的複雜。然而它們對愛滋病的呈現帶有奇觀化的色彩,並隱含如下邏輯:你患病,因為你是性工作者;你患病,因為你是愚昧落後又受貧困所苦的社會底層。而在這些作品的影響之下,愛滋病帶上了性與底層愚昧的標籤,福斯的刻板印象,最終會將痛苦加諸於整個愛滋病群體。
03
恐懼與厭惡交雜福斯視野下,
愛滋病的多重污名化
愛滋病的懲罰隱喻與道德批判,是人們以對抗的視角來理解愛滋病的結果。愛滋病病毒不是我們所接納的自然的一部分,愛滋病人則是與大多數人有所區別的“他者”。在這種隱喻理解的作用下,大多數人對於愛滋病,往往恐懼與厭惡情緒夾雜。
在網上蒐索愛滋病相關的新聞,我們可以看到如下標題:某地艾滋患者10834例:增長減緩,73.5%因男男性接觸;戒毒所裏的愛滋病感染者調查:如何勇敢面對被感染。這些新聞突出某類“高危群體”,加强了愛滋病患者“他者”形象的構建。此外,愛滋病報導通常缺乏患者視角,這也是“他者化”建構的體現之一。新聞傳播學學者楊慧瓊在對2003年至2009年中國媒體愛滋病報導的研究中發現,媒體對於愛滋病防治的報導往往大而空,僅有12%的報導涉及患者和患者家庭;同時,媒體行文傾向渲染患艾的恐怖氛圍,讓患者講述治病的痛苦感受。
新聞報導往往與人們普遍的觀念存在相互建構的關係。另一比特學者孫晶則在愛滋病報導失範研究中發現,媒體對愛滋病患者的呈現並不基於疾病本人和社會事實,在報導時不自覺受到了社會文化偏見的影響。社會文化對於愛滋病的偏見,則集中體現於愛滋病的污名化。
愛滋病特殊的性傳播途徑帶來的聯想,賦予了這種疾病多重的污名。它總是與小姐、同性戀者、吸毒人群等邊緣群體產生聯想關係。污名的過程同時伴隨著懲罰隱喻的影響——對於愛滋病患者,人們總是傾向於猜測他們是否有什麼隱秘的身份和不當的行為。

共亯單車傳播愛滋病的假新聞。
如今,愛滋病群體又承擔了一項新的污名:瘋狂報復的反社會分子。最近網上流傳著這樣一些微信聊天截圖,厭世的愛滋病人說,他以感染他人為發洩手段。他們到處與女性發生一夜情,故意使用破損的安全套。有的人甚至在發生關係後,給女性寄生日禮物並留言道:歡迎加入愛滋病家庭。與“愛滋病”有關的都市傳言還有“艾滋針”。有人說他在共亯單車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發現了針頭,針頭內有愛滋病人的血液。這些流言其實都沒有得到新聞普遍的證實,但人們傾向於“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身上帶有致命病毒的群體,多有“不正當”的行為,是瘋狂的反社會分子,這種刻板印象當然不能代表整個愛滋病群體。此外,性與同性性行為並不是不正當的行為,如果我們能够在觀念中去除濫交等性相關的耻化敘事,將性傳播視作與空氣傳播等途徑等同的管道,那愛滋病是否就不會存在那麼多的污名?
04
關於愛滋病,
我們可以做什麼?
面對愛滋病,人類一直沒有停止過抗爭。
人類醫學在愛滋病攻克領域已經取得了階段性進展。1996年,美籍華裔科學家何大一提出了“雞尾酒療法”,用三種或三種以上抗病毒藥物治療愛滋病,使被破壞的免疫功能部分恢復甚至全部恢復。這種治療對早期愛滋病患者很有效。去年曾有一名在泰國遭遇性侵的網友,在網絡上科普了愛滋病阻斷藥,很多人詫異竟然有這樣的藥物。愛滋病阻斷藥是一種預防藥物,在高危行為發生後72小時內服用藥物可以有效封锁愛滋病毒感染,預防失敗率約為千分之五。
被視為愛滋病傳播主體的衕誌群體,也沒有停止抗爭。國內有相關的衕誌健康公益組織,提供免費的愛滋病毒檢測。去年戛納電影節上獲得好評的同志電影《每分鐘120擊》,講述了上世紀90年代法國衕誌的抗艾之路。一個名叫西恩的男孩,即使病情不斷惡化,依然堅持投入到抗爭之中。雖然西恩沒能看到最終的勝利,但他曾經那樣精彩而熱烈地抗爭過、生活過。

《每分鐘120擊》劇照。
HBO有一部電影叫做《平常的心》。“綠巨人”馬克·魯弗洛和“孔雀”馬修·波莫在電影中飾演一對同志人,激進的衕誌作家內德、“深櫃”的紐約時報記者費尼克斯。電影還原了美國衕誌早期抗艾的掙扎。《平常的心》除了塑造衕誌群體的掙扎之外,還塑造了與之對立的“局外人”——冷漠的政府和醫療機構。這些身處異性戀世界的人,把愛滋病當作一種在衕誌內部因濫交而流行的病,不值得政府關注,不值得研究。申請經費的醫生當場暴怒:非洲已經發現女性感染者,异性性交同樣是傳播途徑之一,很快我們就要都死了,而你們覺得我的研究不够集中不值得撥款?衕誌作家內德在市長辦公室大喊:我們快要死了,你們卻不把它當作一場公共健康危機?

《平常的心》電影劇照。
你也許不是科學家,無法為抗艾做出實質性的貢獻,你也許不是患病群體的一員,無法為自己的利益而鬥爭,那你可以做什麼?答案或許是,不要成為《平常的心》裡面的“局外人”。
置身世外,源於恐懼、源於厭惡的想像。然而我們可以平息無謂的想像,克服對愛滋病的厭惡,這是人類社會文化加諸於這條RNA病毒之上的多餘意義,它的傳播途徑不可耻,它不單單是少數群體的問題,因為少數群體也是整個人類的一部分。
而對於恐懼,即使它無法完全消除,但它也並非一無是處,它能提醒人們日常謹慎小心。恐懼,並不意味著排斥,我們可以學會與恐懼共存。
瑞士漫畫家弗雷德裏克·佩特斯的女友卡蒂和她的孩子是HIV攜帶者。坦白這個消息時,女友十分不安,她非常誠實地替弗雷德里克考慮,不想讓隱瞞的秘密給兩人的關係造成陰影,於是和盤托出。這個消息對於弗雷德里克來說也如同晴天霹靂,但他沒有選擇離開。

《藍色小藥丸》,[瑞士]弗雷德裏克·佩特斯著,陳帥、易立譯,後浪丨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11月。
在描述這段經歷的《藍色小藥丸》漫畫集中,弗雷德里克思考著女友和孩子的未來。日常的恐懼依然存在,生活中很多小細節都可能成為傷害他們的契機,但他發現自己越來越欣賞卡蒂,像她那樣每天面對鏡子審視自己的疾病在他看來難以忍受,“在以往的愛中,我從未有過這種真摯的仰慕之情,我說的不是吸引或者崇拜,而是喚起尊重的欣賞。”而他認為自己對於卡蒂的憐憫,像鞋子裏硌脚的石子。俄國作家契科夫在短篇小說《公差》中借小人物之口,寫出了一種類似的困境:“我們承受生活中最深重的苦難和哀痛,而把輕快和歡樂留給你們,讓你們在坐下來吃晚飯的時候,可以冷靜而頭頭是道地議論為什麼我們受苦和死亡,為什麼我們不像你們那麼健康和滿足。”
弗雷德里克的例子,給予了我們一種新的啟發。面對愛滋病這個怪物,我們依然可以用愛和尊重,實現與恐懼共存。因恐懼而遠離是天性,而在恐懼中擁抱彼此,才是我們追求的閃光人性。

由同名漫畫集改編的電影《藍色小藥丸》(2014)。原漫畫由作者親身經歷改編,講述弗雷德與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相愛、相處的故事。
撰文|安安;
編輯|走走、西西;
校對|吳興發。
評論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