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倒退十年,壓根沒人能想到東北這個落魄的地方,能成為中國文藝創作的富礦。
出現在電影小說裏的上個時代的東北人,必然會承受炒魷魚、離婚、精神失常、甚至兇殺等足以摧毀普通人正常命運軌道的衝擊。
一些所謂的新興中產階級很喜歡閱讀這樣的故事,他們俯視著那些承受苦難的東北人,進而在潛意識裏推匯出一個讓自己感覺非常舒適的結論——
我和那些被時代列車碾壓的前人不一樣,我受過完備的全日制教育、我有足以隨處謀生的知識儲備、我有互聯網賦予的開闊視野,只要我足够努力,他們的命運,永遠不會降臨到我的頭上。
這種審美需求和看驚悚片差不多:那些恐怖的意象是假的,電影一結束,庸常生活便顯得充滿了安全感。
而對這份安全感的追逐,形成了某種文化消費的動力源泉,這兩年關於東北的艺文產品越來越走樣,《漠河舞廳》這首歌的走紅,便是這種潮流的必然產物。
1.
“我從沒有見過極光出現的村落,也沒有見過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殺人又放火…….”
單從這些堆砌華麗辭藻的押韻歌詞,恐怕沒人能理解這首歌到底在唱什麼,不過沒關係,在各種短視頻的文案裏,這首歌的背景故事出現了至少數億次,你想躲都躲不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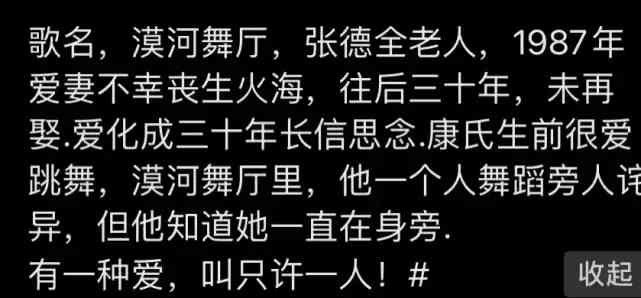
即便你不刷短視頻,這段時間也有諸多媒體,全方位無死角地挖掘了《漠河舞廳》歌曲之外的故事:
一個名為張德全(同音化名)的老人,妻子在1987年漠河“五六大火”中不幸喪生,此後三十年老人並未再娶。妻子生前熱愛跳舞,所以老人常去舞廳中獨舞,思念妻子。
可這些樂評,大規模出現了背後故事淩駕於歌曲本身的喧賓奪主現象。就仿佛一個人要評估一碗過橋米線好吃不好吃時,講的全是過橋米線背後的故事,讓你忘了它本身的食材可能很糟糕,湯底用的也全是廉價調料。
這倒是十分符合保羅·福塞爾對“低俗”的定義。

80年代舞廳,跳著霹靂舞的年輕人
還有一些人說這首歌可以給人帶回1980年代的舞廳。這就更扯了,那時舞廳流行過的金曲,不論是節奏動感的荷東猛士的士高,柔情似水的鄧麗君,還是特別適合交誼舞的《北國之春》,都無《漠河舞廳》這般扭捏的調調。
漠河這座城市,有著濃厚的“他者”意味。它離大多數人的生活的地方都很遙遠,舞廳這種娛樂場所更像是上世紀的遺跡,漠河的舞廳、喪偶的孤獨老人疊加在一起,一個看似可供多角度挖掘的文化IP就這樣誕生了。

但線民對待漠河舞廳,是一種居高臨下的關照,是主流對邊緣的同情,這種情感恐怕無法轉變成與流量相匹配的實際消費能力。
2.
漠河舞廳和張德全老人,本質上和早期好萊塢電影裏的印第安少女一樣,形象確實是正面的,但可惜不能與真正的主角平等。真正的主角是聽歌的人。這些人要做的是取悅自己,也就是自媚、刻奇。
發現故事,關注底層,是一個創作者應有的自覺,但同時稍有不慎,便會因過度解讀淪為大型刻奇遊戲。
從商業角度來說,《漠河舞廳》無疑是成功的,但所有人都忽略了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一比特因大火喪妻的老人,會不會用“殺人又放火”這幾個字來形容愛人的眼睛?
刻奇這個詞,來源於米蘭昆德拉的長篇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可以簡單理解為强行自我感動或强行感動他人。

舉個例子:在新聞媒體工作的朋友,記者節那天應該就經歷了一次集體刻奇表演,朋友圈裏全是最擅長審查和自我閹割的同事過火地歌頌自己的工作,情懷和熱愛,是高頻詞彙。
自我感動最常用的辦法,便是渲染艱難和辛苦,仿佛輕鬆自如是一種原罪,而走一條艱苦卓絕的道路天然散發道德光芒。很奇怪,如果你想讓別人欣賞自己,展現自己舉重若輕的一面豈不是更有效果?
《漠河舞廳》的火熱,便是這種自瀆式刻奇的集大成者,它迎合了這類空洞浮誇且不自知的集體情緒,它無法提供思考,也不能助力判斷,只負責製造速食式的情感共鳴,一股腦地傾瀉相思之苦。
把這首歌代入任何一個場景、任何一段情愛關係裏,似乎都能成立。
當然這也是它的市場如此廣闊的原因,它足够用力,也足够輕浮,以至於每一個失戀者聽完都會長籲短歎:我太難過了,為什麼愛一個人會這麼痛苦?
不,你不痛苦,你畢竟還有在這裡抒情的力氣。
失去摯愛所帶來的痛苦和世界上所有的痛苦一樣,都是無比具體的,命運真開始往死裏搞你的時候,你只有快速處理傷口的焦急,隨後是療愈過程中自然的麻木。就像你智齒發了炎,想的只有儘快去拔牙,而不是捂著腮幫子想寫一首讚美牙醫的詩。
這位張德全老人的妻子,應該是不幸喪生於1987年的大興安嶺火灾,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森林火灾,火場面積達1.7萬平方公里,相當於一個歐洲中等國家大小,並造成211人死亡。
這場火灾是一代人共同的時代記憶,但《漠河舞廳》這首歌,似乎對宏大歷史沒有任何挖掘的興趣,看上去它更關注的是個體情感,可歌詞裏卻充滿替他人代言的無節制主觀抒情,而不是鮮活的細節。
實際上它帶來的只是一份能够取得煽情最大公約數的苦戀,來給抖音裏年輕人的雪地漫步提供足够有格調的BG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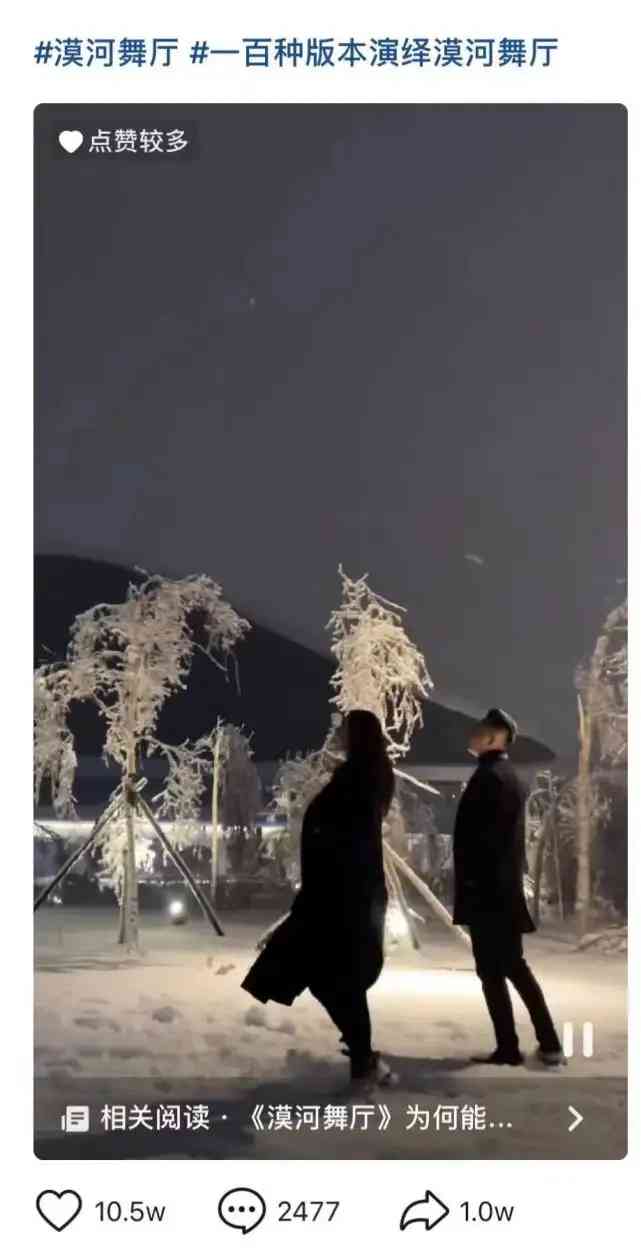
我想起樸樹的《白樺林》,同樣是講述失去愛人的故事,但“誰來證明那些沒有墓碑的愛情和生命”一句,仿佛鏡頭緩緩上升,從白雪皚皚的鄉村轉到炮火連天的戰場,在斯大林格勒、在庫爾斯克、在莫斯科…….衛國戰爭血肉橫飛的鋼鐵洪流中,上演著無數“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的悲劇。

我甚至想起了董寶石的《野狼Disco》,市井小民的幽默和苦澀,欲望和幻想,共同構成了鮮活立體的復古景觀,過去二十多年的東北市民生活,在蒸汽波的伴隨下,像一幅博物館裏的電子動態畫卷般徐徐展開。

所以你問我什麼是好歌,我有一個可能略顯偏執的標準——這首歌一定要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徵,無論是這首歌誕生時所處的時代,還是它想講述的時代。
我一聽這首歌,就能立刻進入到它的時代場景裏,感官或記憶被充分調動,仿佛來到了那段歲月。能做到這一點,這首歌才能堪稱經典。
再過二十年,《漠河舞廳》再響起時,能勾起我對當下這個時代,或對1987年那段歷史的回望嗎?我對此不抱信心。
3.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尼爾·波茲曼提出了“童年的消逝”這一概念,犀利地指出在電視時代,由文字確立的成年人與兒童之間的鴻溝被填平,兒童通過電視,幾乎都被迫提早接觸到充滿衝突、戰爭、暴力甚至性愛的成人世界,“童年”逐漸消逝。
而到了移動互聯網短視頻時代,似乎更明顯的趨勢是成年在消逝。
《漠河舞廳》這麼一首底色悲凉的歌,現在已經成了不少美女主播的走秀BGM,甚至被魔改成了各種版本,大家玩得不亦樂乎,一開始的刻奇感動,逐漸朝著娛樂至死的方向展開,在抖音快手刷這首歌,刷來刷去會感覺這首歌早就變成了一群孩子的共亯玩具。

已經有相當一部分短視頻創作者,壓根不理會任何BGM的歌詞內容,一段劣質抗日神劇的片段剪輯,配上一首不倫不類的戲曲腔言情歌曲;甚至還有把革命英烈的影像資料拿來,配上《漠河舞廳》的奇怪操作。
人們拒絕思考,拒絕閱讀理解,甚至拒絕認認真真聽一首歌在唱什麼,成人特徵逐漸退化,在錯別字和謬誤荒誕的背景音裏盡情遨遊。
互聯網在中國能打造出各種亞文化的歷史,也就十幾年的時間,從早期非主流的粗鄙簡陋,到如今一切為了短視頻服務的壓倒式潮流,工具理性逐漸在大眾文化領域裏佔據上風。
就像你今天聽到的各種古風歌曲,看到的漢服走秀,並不是傳統文化的復蘇,這些勞什子和《漠河舞廳》一樣,是創作者迎合集體刻奇的產物。
我始終對中國是否存在真正的中產階級存疑,但毫無疑問,日子稍微過好一點的人,都在想像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而文化消費,正是到達想像彼岸的最直接途徑。
但許多人想像的中產階級格調,總是和周遭的社會環境格格不入,這種格調的發源地是櫥窗裏的西方或漢唐。可格調是桀驁不馴的動物,沒有經歷系統訓練便妄想駕馭格調,就等於農場新手第一次參加鬥牛,手忙腳亂,也難逃六蹄朝天。
一個可能連《紅樓夢》原著都沒讀過的大學生,穿上漢服唱個古風歌曲,就敢宣稱自己鐵肩擔起了復古道義,哪怕那個歌可能是抄襲得來的;

一個為了坐台小姐能和妻子鬧離婚的小老闆,喝杯茶也要煞有介事地搞出半小時繁文縟節的前戲;
一個能因為情人節戀人不給自己發紅包而考慮分手的年輕人,會宣稱自己被《漠河舞廳》裏喪偶老人的忠誠不渝感動。
我其實對此並不憂心,淺薄和矯飾,是生活這個龐大多面體的組成部分,在任何時代都不曾缺席,就算沒有互聯網,身邊的裝逼犯一樣不會少。只是引發刻奇狂歡的載體,質量變得越來越不過關。
一首漏洞百出的三四流歌曲,在賽博世界裏閃轉騰挪地搶奪流量,只能說明工具雖然在跳躍反覆運算,但人性始終連續可導,你我無能為力。

東北的冬天已經到了,大雪垂直降下,最終會覆蓋一切裂痕。希望遠在漠河的張德全老人能觸碰並享受具備真實質感的生活,不要被外界打擾。也希望我們能够學會創造真正的精神愉悅,這種精神愉悅一定生長於我們真實的生活土壤,並最終能無縫銜接地回到我們的生活中來。
因為我們毫無疑問已經處在劇烈的變局之中,過去兩年發生的變化遠超我輩經歷的前二十年,扎實的審美、自洽的文化,都是未來最寶貴的財富。
評論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