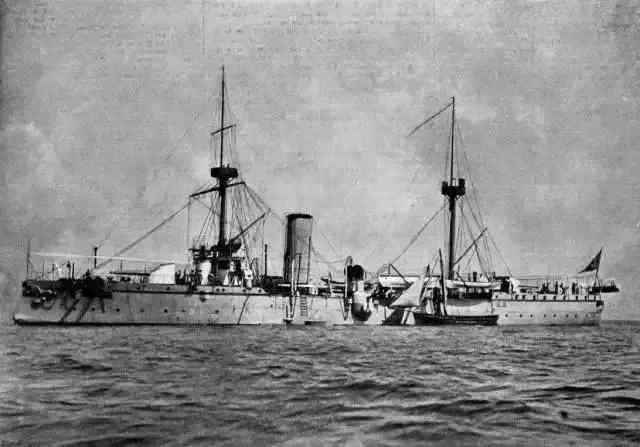

歲月無情,逝者如斯。不經意間,嚴複老先生去世竟然一百年了;在我的淺意識中,似乎還與老先生處於同一個時代。
是時代未變,還是嚴複先生的思想具有極强的穿透性,或超越性?恐怕,二者兼而有之。
就時代而言,我們與嚴複所處並無本質區別,都屬於從農業文明中走出,進入工業社會,但還沒有形成完形工業文明之過渡時代。嚴複所關切的問題,不論古今,還是中西;不論國際,還是國內;就其本質,許多問題都似曾相似,這是既急劇變化,又進二退一,舉步維艱的一百年。
嚴複生於1854年初,咸豐三年底,福建侯官人。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複,字幾道。在他出生那一年,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獲得重大進展,打進江寧,旋改稱天京。此後十餘年,洪秀全坐鎮天京指揮反抗清帝國的運動,震撼全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
太平天國改變了世界與中國的運行軌跡。嚴複也沒有辦法沿著傳統士大夫成長道路繼續前行,中國已經不可能延續農業文明規則,按部就班,固步自封,不與外部世界接觸。這不是中國單方面可以决定的。大航海之後的中國是世界的,世界也是中國的。關鍵是自己如何去理解。
為了應對太平天國的衝擊,清帝國不得不放弃兩百年來的族群歧視政策,允許漢人士大夫組建地方團練,抵抗、打擊太平軍。於是,湘淮勢力崛起,清帝國權力格局囙此發生微妙變化,重大決策不再只是滿蒙貴族集團的特權,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逐漸成為政治舞臺重要角色。
滿漢合力,又有太平天國本身不可克服的內在缺陷和狹隘視野,國際社會主流國家在經過嘗試後也决定不與太平天國合作。太平天國成為“一場未完成的革命”,既沒有推動國家政治轉型,又沒有延續舊軌道建構一個新帝國。
“後太平天國時代”,清帝國無法像鴉片戰爭結束後那樣重回舊有統治秩序,湘淮軍功集團在鎮壓太平天國過程中創建出來的那些軍事工業不可能就此停工,反而因和平到來有了大規模擴充的機會。於是,自强新政各類事業風起雲湧,一個新的時代悄然而至。嚴複後來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個新時代。
當然,如果不是發生重大家庭變故,嚴複肯定會在科舉道路上跋涉,畢竟經過幾代人奮鬥,嚴家已屬小康之家,可以供養他繼續讀書。然而,同治五年(1866),福州當地一場突如其來的霍亂奪去嚴父性命,嚴家失去了頂樑柱,家道中衰,嚴複也不可能繼續一心只讀聖賢書。
當此時,居憂在裏的同邑巡撫沈葆楨奉命創辦船政,以極為優惠的待遇招試英才,儲海軍將才。剛遭喪父之痛的嚴複前往應試,入學考題乃《大孝終身慕父母論》。觸題生情,嚴複以誠摯筆調成文數百,沈公奇之,“用冠其曹”(陳寶琛:《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都統嚴君墓志銘》),年十四,成為福建船政學堂第一届學生,當然也就是中國海軍最早的種子。
古典中國為東方世界的宗主,儘管有漫長的海岸線,也有悠久的航海傳統,但傳統中國並不以海洋立國。尤其是大航海之後,原本並不太弱的航海技術漸漸被束之高閣,以致讓老大帝國極為難堪的兩次鴉片戰爭,均因英法擁有令中國人眼睛一亮的海軍。知恥而後勇。失敗並不可怕。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開始的自强運動,之所以從創建海軍開始,這並不難理解。
而且,那時的中國人也很清楚,甚至曾國藩很早就嘗試過自主創造,當然無不以失敗而告終。科技的創造需要基礎科學的支撐,如果人們看到新東西就能仿造,就能超越,人類就不需要合作,不需要組織成社會。於是,自强新政不僅學西方,而且恭恭敬敬拜西人為師,既來教,又往學,總以學得真經為目的。所以,通觀近二百年中國學習外人的歷史,必須承認學得最好的就是以嚴複、容閎為代表的早期留洋的人,尤其是那些幼童。
福州船政學堂卒業,嚴複那批營員奉派赴英法繼續深造。如果不發生意外,學成歸國,嚴複就是第一批海軍將領。只是人生具有許多不確定,偶然地與某人相識相交,很可能就改變了終生選擇。當是時,出使英法的郭嵩燾與嚴複相見恨晚,結為忘年交,時常相與“議論縱橫”(郭嵩燾《倫敦巴黎日記》534頁),辨析中西學問之异同。嚴複那些非常抗告可怪之論,深得郭嵩燾激賞。於是,不待畢業,郭嵩燾就推薦嚴複提前回國,從“學海軍”改為“教海軍”。先福州,再北洋,匆匆一干就是二十年,按部就班,終昇為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雖沒有海軍將帥銜,但二十年辛苦課徒,實為中國海軍教父級人物。那時,北洋海軍官兵,不是嚴複的學生,就是其同學。

也正是因為這層因素,甲午海戰失敗讓嚴複“大受刺激”(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迅速發表一組檄文,其憤怒遠超同時代任何人。嚴複由一個專業的海軍教育工作者迅速“出圈”,成為那時中國屈指可數的“公共知識人”,享譽朝野。
嚴複認為,中國這一次在黃海的失敗並非偶然,並不是敗在北洋,敗在海軍,而是敗在之前幾十年發展思路和中國人對世界趨勢並不正確的認識。他指出,世界發展已經不是幾十年的樣子了,而主政諸公的腦子並沒有隨著時代而改變,“大家不知當年打長毛、撚匪諸公系以賊法子平賊,無論不足以當西洋節制之師,即東洋得其餘緒,業已欺我有餘。”中國沒有像日本那樣變制改革,誦讀西洋真經,“中國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學問之非,與士大夫心術之壞。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管、葛複生,亦無能為力也。”(《與長子嚴璩書》一)
在嚴複的信念裏,社會發展演變是一個綜合系統,必須按部就班協調發展。落後並不可怕,只要找對了方向,朝這個方向持久用功,即便不一定追上,也不至於跑偏。中國在十八、十九世紀之交那幾十年,確實一度錯過了與西方國家同步發展的良機;但當中國覺醒,開始自己的工業化之後,仍然應該以平常心對待世界,對待自己,無論如何不能老是想著彎道超車,單兵突進,更不能投機取巧,以“後發優勢”的名義拒絕整體協調。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將體用分為兩橛;在嚴複看來,這是中國在甲午失敗最直接、最深層的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說,嚴複是那個時代最先看到自强新政只治其末不治其本,原本想著優勢互補,結果卻是“四不像”,白白耽擱了幾十年光陰。
嚴複指出,優勢互補只是一個理論上的假設,甚至可以說是一個不可能兌現的假說。他舉例說,我們都知道馬的優勢為速度,牛的優勢為負重。按照“中體西用”論者的看法,理想的管道就是將牛的負重與馬的速度重組,創造出既能負重,又有速度的新物種。可能嗎?火車、汽車、飛機等現代運輸工具都做到了,不過這已經不是原物種的強強聯合,而是另外的事情。所以,嚴複強調,一物有一物之用,牛有牛之體,馬有馬之用,僅就物種而言,人們不能理想化地期望牛與馬優勢重組。在紀念嚴複仙逝百年之際,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嚴複社會變化整體性的觀點,以及他對自强新政的敏銳觀察與洞見。
也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嚴複畢生反對激進變革,反對推倒重來,素來主張“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主張一點一滴的改良,主張從最基礎的事情上做起,比如新教育,比如“新民智,新民德,新民力”的嚴氏“新三民主義”。這些功夫做到了,一個現代中國必將悄然而至。而這個現代中國,既有現代世界文明的因數,又有傳統中國文明底色。1905年春,嚴複在倫敦與孫中山晤談說,“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之於丁。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這就是嚴複所信守的漸進改良論,也是嚴複被譽為近代中國保守主義之祖的一個原因。而以“大革命家”自詡的孫中山卻認為,“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侯官嚴先生年譜》)革命與改良,激進與保守,涇渭分明。

先前的研究者以為嚴複早年的思想激進,中年穩健,晚年趨於保守。這個三分法顯然沒有真正理解嚴複思想的進路。所謂嚴複的早年,其實也不算早,甲午戰爭爆發時,嚴複已經年届不惑,他那時不止是激進,簡直就是憤怒,就是狂躁,因為他看到自己的學生、自己的同學,在這場不該失敗的戰爭中丟掉了寶貴的生命。時代的一個微小錯誤,對於個體生命而言就是毀滅。這不能不讓嚴複憤怒。
憤怒出詩人,憤怒也能出政論家。嚴複在那不太長的時間段集中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强》、《辟韓》、《救亡决論》,數量不多,影響巨大,這幾篇文章奠定了嚴複在近代中國啟蒙思想史上不朽的歷史地位。文不在多,有料則靈。
在這些文章中,嚴複比較早,也比較深刻解讀了中國失敗的根源,而且借著這次失敗的機緣,比較暢快地對照分析了中西社會與文化的异同。就其總體而言,嚴複此時對西方近代文明確實看得比較高,對於中國傳統文明,更多的看到了問題。他的一系列比較深刻啟發了後續的觀察者,直至今日,也不能不承認嚴複是近代中國最懂西方文明,又理解中國文明之第一人。比如,在《論世變之亟》一文中,嚴複這段論述直至今日依然贏得人們的稱許:
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勝不可複衰,既治不可複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蓋我中國聖人之意,以為吾非不知宇宙之為無盡藏,而人心之靈,苟日開瀹焉,其機巧智慧,可以馴致於不測也。而吾獨置之而不以為務者,蓋生民之道,期於相安相養而已。
在嚴複看來,生民之初所面對的問題東西並無二致,只是到了後來漸行漸遠,走上各自不同的路。而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就在於“自由不自由异耳”:
中國理道與西方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謂之相似則可,謂之真同則大不可也。何則?中國恕與絜矩,專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則於及物之中,而實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於是群异叢然以生。粗舉一二言之,則如:
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
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
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
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
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
中國多忌諱,而西人重譏評。
其於財用也:
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
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歡虞。
其接物也:
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
中國尚節文,而西人樂簡易。
其於為學也:
中國誇多識,而西人尊新知。
其於禍灾也:
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
若斯之倫,舉有與中國之理相抗,以並存於兩間,而吾實未敢遽分其優絀也。
嚴複從倫理、社會、政治、風俗、知識生產等諸多方面分析了中西文明异同,是近代中國最經典表述,影響深遠。
在《論世變之亟》之後,嚴複又發表一篇更具震撼力的《原强》,探究中國何以在經歷了幾十年自强新政之後依然如此孱弱,如此不堪一擊。嚴複指出,西方國家在過去兩百年突飛猛進,並不只是形而下的堅船利炮、聲光電化,而是另有一種精神在,“彼西洋者,無法與法並用而皆有以勝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觀之,則捐忌諱,去煩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勢不相懸,君不甚尊,民不甚賤,而聯若一體者,是無法之勝也。自其官工商賈章程明備觀之,則人知其職,不督而辦,事至纖悉,莫不備舉,進退作息,未或失節,無間遠邇,朝令夕改,而人不以為煩,則是以有法勝也。其民長大鷙悍既勝我矣,而德慧術知較而論之,又為吾民所必不及。故所謂耕鑿陶冶,織紉樹牧,上而至於官府刑政,戰鬥轉輸,凡所以保民養民之事,其精密廣遠,較之中國之所有所為,其相越之度,有言之而莫能信者。且其為事也,又一一皆本於學術;其為學術也,又一一求之實事實理,層累階級,以造於至大至精之域,蓋寡一事焉可坐論而不可起行者也。推求其故,蓋彼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
嚴複“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不僅是其對西方富强原動力的判斷,也給中國指出了一條極為清晰的道路。中國如果要富强,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就要完全釋放社會,解開人們身上的全部枷鎖,在一個完全自由的空間中,讓中國人的聰明才智獲得充分施展。全面的自由,就是人們可以使用自己的腦子思考,使用自己的眼睛觀察,使用自己的嘴巴講話,自由居住,自由就業,在不違背公序良俗前提下,享有充分的自由。

“自由為體,民主為用”,其實就是說要標本兼治,尤其是要不懈提升“民智、民力、民德”,用漸進的改良推動社會持續進步,“不為其標,則無以救現時之潰敗;不為其本,則雖治其標,而不久亦將自廢。標者何?收大權、練軍實,如俄國所為是已。至於其本,則亦於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開,民力日奮,民德日和,則上雖不治其標,而標將自立。何則?爭自存而欲遺種者,固民所受於天,不教而同願之者也。”(《原强》)
嚴複的這些言論,給人們以極大震撼,啟動了知識界對傳統的重新認識,以及對西方文明本質的再檢討。更重要的還在於,嚴複緊接著向中國人傳遞了進化的觀念,這個影響在很大程度上規範了後來中國人的世界觀、知識論。
進化的觀念在中西都有久遠的歷史,胡適的《先秦名學史》大致梳理了中國古典進化思想的脈絡。嚴複之前的《萬國公報》等,也對西方的進化思想有過不少介紹。但是,真正引起中國人震撼,影響此後幾代中國人的,還是嚴複1898年前後逐漸發表的《天演論》。
《天演論》的原本及嚴譯細節,這兒就不展開論述了,這方面的研究特多。我想強調的是,在甲午戰後相當多的中國知識人極端失望的背景下,嚴複傳遞過來的進化論,明白告訴人們現在的世界就是一個大叢林,眾獸共處,弱肉强食,要想在這個叢林中存在下去,就必須遵守“叢林法則”。叢林法則無他,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八個字。叢林不相信眼淚,只相信實力。這個思想在此後影響極為深遠,所謂救亡,所謂圖存,所謂復興,所謂強國,其實都是這個思想的物化、具化。
嚴複傳導的進化論,帶有很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味,這對於那時的中國人給予很强烈的刺激,先前自大狂妄的“天朝上國”意識受到了沉重打擊,中國未來能否存續,端賴中國人能否擺正心態,走進叢林,參與競爭。
此時的西方資本主義處於發展早期,早期資本主義有許多不規範,許多不道德,但資本主義唯一長處就是沒有東方儒家式的溫情,只有競爭,只有做得比別人好比別人强,才能存活下去,才能獲得發展。這樣慘烈的競爭當然也有問題,財富的少數人佔有與多數人的相對貧困、絕對貧困之間的衝突;富國愈來愈富,窮國越來越窮,也不容易緩解。嚴複看到了資本主義體制的這些衝突,只是這些衝突的解决不能消極等待,坐享其成,唯一的解决之道,在嚴複看來,就是積極參與國際大循環的競爭。
傳統儒家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因而中國社會長時期處於低水準狀態。如果說中國與西方密切接觸之前這種均平主義還有存在空間的話,比如新王朝、新君主的均田、均貧富措施,但到了大航海之後,全球逐步一體化之後,中國的“均富”傳統就不可能繼續存在。重建新的規則,重建新的價值觀,也就是中國走向現代的關鍵一步。嚴複傳遞的進化論,起到了極大的助推作用。思想的力量,在這一點上反映最為明顯。
在西方,思想啟蒙走在社會變革前面;在中國,情形有點不一樣。甲午失敗讓中國付出極大代價,尤其是允許外國資本在中國通商口岸自由開工廠。這一方面,讓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甚至包括條約簽訂者李鴻章這樣極具世界眼光的人無法接受;另一方面,包括李鴻章在內,幾乎沒有中國人預料到,允許外國資本在通商口岸自由開工廠的另一層意義,讓中國的資本主義迅即發生,一個全新的不同於農業社會的地主,也不同於前資本主義時代那些先富階級迅即出現。中國社會迅速發生變化,出乎所有人的預料,不論中外。嚴複傳遞的進化思想、競爭意識,極大滿足了急劇變化的中國社會對思想的需求。這是嚴複的幸運,也是中國的運氣。此後不二十年,中國資本主義就逐漸躋身於世界,至歐戰爆發,中國資本主義釋放出的動能已經可以給世界以影響。嚴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思想應該有一份功勞。這是我們紀念嚴複應該強調的另一點。
第三,紀念嚴複,我覺得還要注意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現在都把嚴複譽為近代中國啟蒙思想家。啟蒙思想家是一個群體,並不是嚴複一個人,只是嚴複起到的作用相對最大而已。中國的思想變動在社會變動之後,許多觀念都是先有事實,再有補課。這是近代中國不同他國轉型的一個突出特點,緊趕慢趕,邊發展邊補課便完善價值觀。

嚴複對近代中國啟蒙思想的突出貢獻,是提供了近代國家建構模型。他認為,近代國家的根本要旨不再是傳統中國的“保育政策”,一切由政府包攬,而是相反,還權於民,還權於社會,“自由為體,民主為用”,只要所有的產業向全體國民充分開放,社會就能找到自己的平衡點。在嚴複的概念中,每一個人的自由是國家發展的前提條件,中國人一旦享有充分的自由,享有與西人一樣的自由,那麼中國的教育、技術進步、經濟增長、國民意識,都會在充分競爭背景下漸趨於與世界一致。自由,在嚴複那裡具有最根本的意義。這是我們紀念嚴複最值得注意的。
自由是發展的保障,壟斷是社會窒息的原因。大航海之後,全球一體化逐步加快,許多新業態不經意就成為一個重要的領域。甲午之前,中國也有傳媒業,上千年的邸報就承擔著傳媒的功能,到了近代,也有傳教士在中國創辦的新聞紙比如《萬國公報》。然而,由於制度滯礙,甲午戰前中國人並不能自由辦報自由言說,這一個新業態就毫無意義。甲午後,釋放社會,釋放黨禁,擴大言論空間,允許自由結社,允許自由言說,很快中國的面貌完全不一樣了,政黨勃興,報館林立,這不僅容納巨大的就業,而且極大啟動了人的創造性,眾聲喧嘩,貌似混亂,其實給政治家政治決策提供了更多的智慧資源。至於個人,因政黨、媒體等業態成名成家者更是不計其數。嚴複就是這個過程層中的獲益者。甲午之後不久,嚴複就逐漸脫離體制,成為以言說、撰文、翻譯為謀生途徑的自主就業者。
自由為本,民主為用,不是一句空話,而是可以落地的構想。嚴複的這一思想一百多年來受到知識界高度重視,只是由於此後的政治環境再轉再變,自由為本的理想漸去漸遠。但我始終相信全球一體化終將打破對自由的遏阻。嚴複的理想一定會落地生花。

評論留言